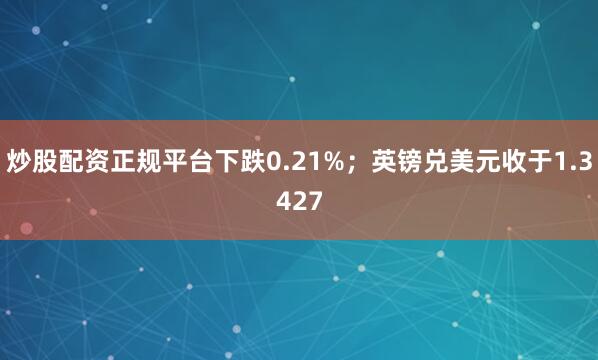第二十届南峰杯征文比赛
获奖作品展播(1)
第二十届南峰杯征文比赛已经圆满结束,随着馆君的步伐一起来看看获奖文章吧~
《土脉》
作者:阳佳杰 未来技术学院
春分后的第一场雨落在晓霞山麓时,祖父正在院坝补箩筐。篾刀破开老竹的声响混着雨打桑叶的节奏,像首不成调的采茶谣。他膝头压着开裂的藤筐,指节被篾刀磨得发亮,像是抹了层屋前溪边的鹅卵石浆。太爷爷教他的诀窍,在青竹第三道节疤下刀,能剖出三指宽的匀称篾条。
“竹要挑背阴坡的,韧劲足。”祖父把篾条在井水里浸透,水珠顺着竹纹滚落,在泥地上洇出几颗北斗星。井台边的苔藓吸饱了水汽,绿得能掐出汁来。我蹲在檐下择秧盘,塑料格子里挤满珍珠糯的嫩芽,根须纠缠如衡山云雾。远处田间刚敷上地膜,银白波浪间浮动着戴斗笠的人影,恍若神仙撒在绿绸缎上的棋子。祖母在灶屋剁腊肉,砧板咚咚声惊飞了屋檐下的燕子,它们掠过祖父新补的箩筐,翅膀尖扫落几片碎篾,飘进雨帘里成了透明的鱼。
展开剩余71%清明前的洣水河总裹着层纱。祖母天不亮就背着竹篓去河滩撬藠头,胶靴踩在卵石滩上的脆响惊起白鹭。沾着露水的藠头根雪白肥厚,她教我辨认叶鞘上的紫晕:“带红紫色斑的才够辣,配衡山豆腐正好。”我们蹲在鹅卵石堆里,江水漫过脚踝的凉意顺着脊梁往上爬。对岸采沙船突突作响,河中的商船、货船也轰隆隆的船来船往,好生吵闹。腌菜坛沿水咕嘟冒泡时,满屋子都是冲鼻子的辛香,熏得窗台上的豆芽直打晃。祖父说这味道能驱邪,把开了裂的犁头铁片浸在坛沿水里,来年春耕就不会崩刃。
夏至晌午,晒谷坪成了炼丹炉。祖父赤膊翻动稻谷,汗珠子落在水泥地上瞬间化作白烟。他肩胛骨晒得黢黑,脊椎沟里积着层盐霜,像晓霞山裸露的岩脉纹路。蝉在苦楝树上扯着嗓子嚎,稻芒沾在后颈上,痒得如同蚂蚁排队过山。我抱来新收的艾草扎把,青烟腾起时,整座山谷都跟着稻浪摇晃。祖母突然指着西边说:“看,回雁峰显影了。”可我们谁都没抬头——晒场上的粮食比菩萨更怕乌云。去年暴雨来得急,抢收的稻子堆在堂屋发了芽,熬粥带着股酒糟味,祖父蹲在门槛抽着壶烟,火星子把夜色烫出个窟窿。
秋分夜砍紫云英最磨人。露水把裤管打得精湿,镰刀掠过草茎的沙沙声惊起草蜢。月光给绿肥田铺了层银霜,祖父说这是给土地盖被子。他把绿肥铺成八卦阵,说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法子。腐熟的茎叶混着红壤,发酵出南岳腐乳般的气息。我弯腰捧土时,忽然摸到半块带绳纹的陶片,祖父眯眼瞅了瞅:“许是祝融庙的香炉渣。”他讲起太爷爷那辈人,扛着香烛爬三十里山路去南岳朝圣,背篓里装着新收的茶油和腊肉。现在高铁隧道从山腹穿过,香灰都落不进祝融殿前的青铜鼎。
小寒刨冬笋要听山音。祖父敲着竹棍在毛竹林里转悠,靴底沾满黄黏土。枯叶下的笋尖刚冒头,他下锄时忽然顿住:“下面有竹鞭横着,这笋留着当引子。”去年他挖断了主鞭,半片竹林没发新笋,被祖母骂了一晚上。灶膛灰烬里煨熟的冬笋剥开来,芯子金黄如南台寺的琉璃瓦。祖母往我碗里夹笋尖:“吃吧,这是山神爷的指甲盖。”窗外寒风夹着雪粒,打在窗户外的玻璃上,叮叮当当响了一夜。
谷风车在老房子的角落又转过三载春秋,轴承间的泥沙渐渐被时光碾成齑粉。墙上的日历撕到乙未年那页,祖父的篾刀突然在某个清晨哑了火——它卡在半截发霉的青竹里,刃口锈斑蜿蜒如干涸的田垄。祖母把浸藠头的陶瓮挪到后房时,听见智能手机在抽屉里震动,父亲从省农科院捧回的太空莲种子,正在锡箔袋里做着发芽的梦。
前年谷雨回老家,父亲正给新育的太空莲分株,听说这是基因工程带来的新品种。洣水引来的渠水汩汩漫过莲田,他赤脚站在泥里,裤脚绾成采药人的绑腿式样。去年试种的莲蓬大如海碗,莲子掉进淤泥,今年竟自发地长成北斗七星的阵势。"莲蓬要留七分空,太满招蛀虫。"他掐掉过密的叶芽,动作像在给菩萨理袈裟。无人机在邻田撒种,父亲扛着铁锹笑道:"这铁鸟再能耐,也闻不出倒春寒的膻气。"他摊开手掌,老茧纹路里嵌着洣水河上游特有的赭红色泥沙,像幅微型山水画。
前几天夜晚视频时,父亲举着手机带我“巡田”。镜头扫过挂满蛛网的农具,在老房角落的谷风车上停了停——那是我儿时最爱的玩具,手柄处还留着牙印。他忽然蹲下拍田埂:“瞧,去年你说的紫云英,把蚯蚓都养胖了。”月光漫过晓霞山的轮廓,在他白发上铺开一层霜。我听着二十里外洣水的夜航船鸣笛,忽然明白祖父那句话:庄稼人接的是地气,养的是土脉。父亲的白发是盐碱地,我们的记忆是蚯蚓,年复一年翻动着这片土地深藏的魂魄。
此刻我在城市阳台上种百合花,塑料盆里的红壤正悄悄板结。浇花时总恍惚听见祖父篾刀破竹的脆响,混着祖母剁腊肉的咚咚声。手机弹出父亲发来的照片:新栽的太空莲浮在如镜的池塘里,倒映着南岳七十二峰青黛色的影子。莲叶下聚着细小的气泡,那是泥土在呼吸。我数了数,恰好七颗,北斗七星落进了人间的水田。
发布于:北京市配资实盘平台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